|
|
小编荐语
本期栏目继续摘编评述近年来国外主要法学刊物刊载的财税法学术论文,选取美国西北大学普利兹克法学院主办的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Law Review 的三篇文章,推出“税收与经济社会的交互作用(下)”专栏。
构建现代税收法律制度需要更深刻地理解法律与经济基础、政治及社会秩序间的交涉性平衡关系。在上期专栏中,本栏目摘述的两篇文章讨论了税制设计对外部经济社会在危机应对与发展促进等方面的作用与影响。本期专栏将从另一面继续这一话题,推介有关经济发展、财政结构以及社会秩序对税法改革影响的研究成果。
从经济发展的角度,康奈尔大学法学院助理教授 Eleanor Wilking 通过对美国所得税申报数据的实证分析,论证了当前数字时代灵活就业趋势下改革美国所得税制度对雇员和独立承包商进行二分法处理的必要性。从财政结构角度,美国西北大学普利兹克法学院教授 Ajay K. Mehrotra 回顾了美国现代财政史上讨论开征增值税的三个关键时期,认为美国长期以来财政收入结构与社会福利支出结构的分裂是其抵制开征增值税的根源所在,其特有的财政结构对税制发展的“锁定效应”使美国成为世界财政发展进程中的“例外主义”。从社会秩序的角度,美国匹兹堡大学法学院教授 Anthony C. Infanti 着眼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对Windsor案的判决,指出了其利好同性婚姻伴侣享受平等税收待遇背后产生的税收不确定性及程序负担等后果,警示了税法在回应社会价值变迁、追求平等时需要均衡考虑多项基本原则与多方现实利益。
目录
专栏 税收与经济社会的交互作用(下)
01 法律和事实中的独立承包商:来自美国纳税申报表的证据
02 缺失的美国增值税:经济不平等、美国财政例外论以及美国历史上对国家消费税的抵制
03 税收平等的荒凉面:温莎案及其之外
专栏 税收与经济的交互作用(下)
1
法律和事实中的独立承包商:来自美国纳税申报表的证据
Independent Contractors in Law and in Fact: Evidence from U.S. Tax Returns
来源 |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Law Review, vol. 117, no. 3, 2022, pp. 731-820.
作者 | Eleanor Wilking(美国康奈尔大学法学院助理教授)
美国联邦税法根据服务购买者(即企业)对员工的控制程度,将其分为两类:雇员(employee)和独立承包商(independent contractor)。界定所属分类的重要标准是员工还是企业对工作具有更多的控制权(control)。这种分类带来了重要的税收和监管后果,决定了员工需要支付的税种、缴税方式、税收补贴、侵权责任、企业的监管成本、工作场所安全和反歧视保护等。
但是,应该如何衡量控制权这样一个复杂多维的概念?文章指出,目前美国国税局和其他联邦机构用于区分雇员和独立承包商的多因素平衡测试(multifactor balancing test)成本较高且具有内在的不确定性。该测试涉及多达20个不同的因素,由于对这些因素的判断存在主观性,且缺乏利用这些因素来归类员工的公式。两个面临基本相似的经济和关系情况的员工可能被归为不同类别,这为企业提供了可选择性。但是,该测试为企业提供了多大的灵活性?该测试的政策反应如何?企业实际上如何对员工进行分类?对于这些重要问题,此前并无基于实证数据的研究。
为此,文章基于2001年至2016年之间所有被数字化的美国所得税申报数据,引入了对实践中企业如何对员工进行税收分类的实证研究。首先,文章探讨了企业对员工的分类与控制权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是如何随时间演变的。其次,文章衡量了在不同政策下独立承包商身份对企业的吸引力变化及企业的政策反应。联邦税法下确定分类的关键标准是行为(behavioral)、关系(relational)和财务控制(financial control),文章则使用雇员和独立承包商在描述他们与企业关系时在收入依赖性(income dependence)、支付者数量(number of payers)、与支付者的距离(distance to payer)、任期(tenure)、报酬波动性(compensation volatility)和扣除(deduction-taking)这六个维度上的不同作为代用指标,利用所得税申报数据,通过企业的分类决定分析企业是如何对使独立承包商的成本低于雇员的政策做出反应的。
这一分析得出了三个不同的发现:首先,在2016纳税年度,雇员和独立承包商在大多数衡量标准下没有明显区别。其次,自2001年以来,雇员和独立承包商在上述六个衡量标准下已经趋于一致。例如,大多数雇员和独立承包商表现出类似的收入依赖程度,且这种趋同在收入较低的员工中尤为明显。第三,企业对员工的分类受到多因素平衡测试以外因素的影响,包括雇员和独立承包商的相对监管成本。例如文章发现,当小企业(全职雇员不超过20人)的雇员年满65岁时,医疗保险的使用会优先于其雇主提供的健康保险费用,从而为企业节省资金;然而,当大企业的雇员年满65岁时,会优先使用其雇主提供的健康保险费用,从而激励企业将员工重新归类为独立承包商。为应对这一政策,企业可能会选择操纵对员工的分类,或者通过实质性地重新配置他们的生产过程来满足多因素平衡测试的要求。但是,文章认为,无论哪种反应都是不可取的——前者违反了基本的横向公平原则,员工被归类的方式和“企业-员工”关系的实质之间的错位加剧,独立承包商和雇员的边界愈加模糊;而后者则扭曲了行为,使之偏离了没有监管变化时的最优状态。
最后,文章讨论了划分独立承包商和雇员的法律边界被明显侵蚀所引起的规范性问题。文章提出,独立承包商和雇员的分界类似于 David Weisbach 教授提出的“柏拉图式的概念”(platonic notions),分界的判断依赖于容易被操纵的因素,从而导致所涉主体根据自身利益作出行为选择。雇员和独立承包商越是相似,就可以越清楚地发现税收制度对这些群体的区别对待是没有合理依据的。文章认为,目前,自营职业的门槛降低,劳动力市场动荡加剧,技术变革即将到来,现有的区分雇员和独立承包商的界限将愈加模糊,有必要重新评估所得税制度对员工的二分法处理。

2
缺失的美国增值税:经济不平等、美国财政例外论以及美国历史上对国家消费税的抵制
The Missing U.S. VAT: Economic Inequality, American Fiscal Exceptionalism, and the Historical U.S. Resistance to National Consumption Taxes
来源 |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Law Journal,vol. 117, no. 1, 2022, pp. 151-190.
作者 | Ajay K. Mehrotra(美国西北大学普利兹克法学院教授)
文章使用历史分析的方法论证美国长期以来财政收入结构与社会福利支出结构的分裂,是导致其抵制征收增值税的根源所在。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经济不平等的现象在全球范围内不断加剧,社会财富集中于上层群体的比例上升而底层群体的生活状况未明显改善。作为发达国家的美国,收入分配不均的程度在OECD成员国中排名第二,经济不平等问题亟待解决。理论上,利用财税政策均衡收入分配是收效明显的措施,而美国却一直面临“税负过重”的政治障碍,难以借助改进税制结构来抑制不平等状况的发展。文章指出,美国“税负过重”并非事实,而是由其“直接税占比重、社会福利产出形式隐晦”的财政结构特性所误导的假象。“税负过重”的观念已然成为一种刻板印象,致使美国难以通过诸如增值税等一般消费税筹集更多收入以支应政府再分配。在世界各国以包括增值税在内的平衡税收结构为社会支出提供资金的背景下,美国的税收收入来源是一个独特的“例外主义”。
文章进一步分析了美国“税负过重”认知误区背后的特有财政结构原因。一方面,与其他大多数先进的工业国家以直接税与间接税平衡结合的税制结构相比,美国联邦财政收入整体上更依赖直接税,其2019年所得税和工资税占联邦财政收入总额的比例达到93%。而美国以纳税申报和代扣代缴为基础的所得税制度,使纳税人能够更加清晰地感知到毛收入与净所得之间的差异,税痛感更为明显,加剧了纳税人和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因此任何新税种的引入都或多或少伴随着民众的抗议。另一方面,不同于其他国家基于公民身份提供社会保险和福利待遇,美国一般通过税式支出、公私合作伙伴关系等间接途径提供“隐形福利”。例如,美国一般根据纳税人的就业状况和纳税额度,给予公众免税或减税待遇,包括反贫困税收政策的典型——劳动所得税抵免(EITC),相较而言这对个人收益的加额效应不明显;美国还通过大量私人组织向公众提供公共服务和社会救济,同样弱化了民众对政府财政支出使用于公共领域的感知。
对民众而言,强汲取性的财政收入结构和隐晦性的财政支出结构,造成了美国“税负过重”的惯性认知,进而在税制发展中形成了“锁定效应”,使得任何带有潜在加税效果的改革建议都难以成行。事实上,根据OECD公布的税收数据,2020年,美国的总税收占GDP的比例为25.5%,远低于OECD成员国近34%的平均水平,也远低于法国(45%)、英国(33%)、德国(38%)等其他发达国家,而这种差距自1965年以来就未曾发生变化。但正是由于美国纳税人能够感受到直接税的“剥夺”,却容易忽视“隐形”的社会福利,致使美国历史上多次尝试征收增值税以拓展财源的尝试均以失败告终。
文章回顾了美国现代财政史上讨论开征增值税的三个关键时期,并总结出各个时期的社会背景均刺激美国政府改革税制结构,但民众、商业团体和政客等群体却成功阻止了美国国会推行增值税。第一次重要尝试发生在一战后,战时美国大幅提高联邦所得税率并减少免税减税措施,战后美国仍有大量资金需求以应对战争债务、退伍军人抚恤和经济重建。耶鲁大学政治经济学家 Thomas S. Adams 提出的增值税设想却并未获得国会民意代表的认可,也受到商业组织有关累退性和税基不稳定的质疑,最终未能施行。第二次重要尝试是在美国经济大萧条和二战爆发期间,经济衰退重创美国联邦财政收入,美国意欲寻求增加收入和平衡预算的有效方案,故胡佛政府再次提出开征一般消费税。然而,美国众议院筹款委员再次被团体组织的意见说服——美国劳工联合会和农业局联合会均表示强烈反对,抵制一般消费税链条式征税对各个经济环节的普遍负担;而零售商群体也反对开征联邦层面的终端零售环节一次性销售税,认为这会加大负担并抑制消费。第三次重要尝试是在20世纪70年代,尼克松政府打算推行联邦增值税取代地方财产税,以更充足的收入为各类社会保障项目提供财源,最急需支援的就是学前及中小学教育融资。此时,抵制增值税已具有明显的“锁定效应”,反对者更包括美国许多州长、市长和地方财政官员,尽管其深知开征增值税将提升地方社会福利的作用。
文章最后指出,财政结构上的特性导致美国无法借助一般消费税改革获得充足收入以向政府再分配提供资金,致使不平等现象加剧。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等发达国家均在上世纪克服政治反对意见而推行了增值税,而美国却长期受制于“税负过重”认知的锁定效应,成为世界财政发展进程中的“例外主义”,这将增大其应对经济不平等的困难。尽管在平衡收入分配方面,开征增值税可能并不是一个必要的步骤,但文章认为,除提高最高边际税率、取消对资本利得的优惠、征收新型财富税等向富人加税的改革措施外,通过开征增值税并向中下层群体提供更多的物质支持也将是值得探索的路径。

3
税收平等的荒凉面:温莎案及其之外
The Moonscape of Tax Equality: Windsor
and Beyond
来源 |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Law Journal,vol. 108, no. 3, 2014, pp. 1115-1135.
作者 | Anthony C. Infanti(美国匹兹堡大学法学院教授)
文章讨论了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对 Windsor 案的判决,认为其尽管加大了美国同性婚姻伴侣可享受平等税收待遇的可能,但却从另一个层面提高了同性伴侣在税收问题上面临的不确定性。尽管该主题的讨论和研究背景已于2015年美国最高法院裁定同性婚姻合宪且美国全境承认同性婚姻效力后发生了改变,但文章提出的观点和视角对税法研究仍有价值,即应关注基于外部政策而促成的税法规则所隐藏的潜在负面效应。
文章首先概述了美国1996年《捍卫婚姻法案》第3条有关“婚姻”和“配偶”的规定在税务征管中引发的争议及其重要判例。《捍卫婚姻法案》第3条规定,“婚姻仅指一男一女作为丈夫和妻子的合法结合,配偶仅指作为丈夫或妻子的异性”,这剥夺了同性伴侣享受基于婚姻关系可获税收优惠待遇的机会。例如,在 Dragovich 案中,一群加州公职人员质疑《捍卫婚姻法案》第3条阻碍了同性伴侣加入该州长期护理计划并享受联邦税收优惠。而文章主要探讨的 Windsor 案,涉及两位在美国纽约州登记为“同志伴侣”并在加拿大安大略省登记结婚的女士,其中一人去世后将房产留给另一人,而美国国税局却认为后者不可享受美国联邦遗产税针对配偶继承房产免税的优惠,应缴纳约36万美元的遗产税。在纳税人提起的申请返还税收诉讼中,美国地方法院认为“在未亡同性配偶因无法获得遗产税婚姻减免资格而被要求承担联邦遗产税的情况下,《捍卫婚姻法案》第3条侵犯了未亡同性配偶的平等保护权利”。美国最高法院9位大法官在该案的上诉中以5:4的多数意见作出裁决,同样认定《捍卫婚姻法案》第3条无效,原因是“婚姻相关法律的任何目的都不能超越对人格尊严进行保护免受贬低和伤害的需要”。此后,奥巴马总统指示美国国税局“寻找方法确保同性伴侣获得应有资格所获的福利”;两个月后,美国国税局发布指导意见,说明“两名同性自然人在承认同性婚姻的州缔结婚姻后即可认定为基于税务目的有效的婚姻关系,即使他们目前居住在一个不承认同性婚姻有效的州”。
文章认为,上述看似同性伴侣平等权利保护取得重大突破的进展,却使得同性伴侣在所得税等税务申报和优惠待遇问题方面面临的不确定性倍增。在 Windsor 案前,《捍卫婚姻法案》第3条使得同性伴侣不能提交联合联邦所得税申报单,但美国国税局也并未明确其是否可按其他方式联合报税及税务后果,这已然成为不确定性的来源之一。在 Windsor 案后,由于《捍卫婚姻法案》第3条被宣告无效,同性伴侣是否被视为已婚将根据《捍卫婚姻法案》第2条参照各州法律予以确定。当时美国各州对同性婚姻效力的认可程度不一,有的州允许同性伴侣结婚,有的州不允许缔结同性婚姻但允许建立与异性伴侣权利义务平等的民事结合关系,有的州不允许缔结同性婚姻且规定同性伴侣建立民事结合关系所产生的权利义务低于异性婚姻,有的州全面禁止同性伴侣结婚和建立民事结合关系。这种复杂的局面使得美国国税局在 Windsor 案后的指导意见存在诸多适用漏洞,引发“棘手的法律选择问题”,反而增加了同性伴侣在处理税务问题上的负担。
其一,“规避法律的婚姻”的认定及其税务后果问题。美国国税局认为,基于税务目的判断同性伴侣结婚是否有效,应参照同性伴侣的婚姻缔结地法律而非居住地法律。但这可能涉及所谓“规避法律的婚姻”,即一对同性伴侣在一个不承认同性婚姻效力的州生活,前往另一个允许同性结婚的州缔结婚姻关系后又立即返回原居住州,该缔结婚姻的法律行为根据《美国第二次冲突法重述》的规则很可能被原居住州认定为无效。美国国税局的指导意见忽略了这一常见的情形及其后续的税务后果,看似实现平等的同时却可能忽略了实际负担。其二,同性伴侣与其子女关系的认定及其税务后果问题。一对同性伴侣在允许同性结婚的州缔结婚姻后,如迁至不承认同性婚姻的州生活,尽管他们的税务事项可按配偶关系进行处理,但其如若代孕或收养子女,他们和子女之间的关系是否能得到法律认可并适用亲子关系进行申报纳税,同样存在极大不确定性。其三,美国国税局的指导意见仅关注了“同性婚姻关系”,而实践中常见的“民事结合关系”(civil union)和“家庭伴侣关系”(domestic partnership)的税务处理却没有对应的规则,不仅影响建立此两类关系的同性伴侣的税务负担,还可能在同性关系建立的个体选择方面产生扭曲效应,加重缔结婚姻重要性的刻板印象,不利于促进更多元关系的社会承认。其四,当有效缔结婚姻关系的同性伴侣来到不承认同性婚姻的州生活时,需要该州税务部门的配合才能成功报税并申请优惠待遇,因为该州过往可能并未处理过有关同性伴侣以婚姻关系申报纳税的案件,这增加了纳税人与税务部门的合规负担。
文章认为,一项令人欢欣鼓舞的法院判决以及行政部门的解释函件,其中潜藏的漏洞却使得同性伴侣需要就税务申报问题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如其缺乏专业知识可能还需聘请或咨询专业税务人士帮助解决,徒增其纳税成本。因此,在税法规则的设计中,需要均衡考虑多项原则与多方利益,避免因简单的追求平等的诉求而忽略了现实的纳税实体及程序负担。

整理 / 张 旭、娄佳璐
排版 / 罗仪涵
审核 / 张 旭

北京大学税法研究中心
Peking University
Center for Tax Law

长按二维码关注我们 |
-

|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35448号
( 京ICP备19053597号-1,电话18600416813,邮箱1479971814@qq.com ) 了解Tax100创始人胡万军
优化与建议
隐私政策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35448号
( 京ICP备19053597号-1,电话18600416813,邮箱1479971814@qq.com ) 了解Tax100创始人胡万军
优化与建议
隐私政策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35448号
( 京ICP备19053597号-1,电话18600416813,邮箱1479971814@qq.com ) 了解Tax100创始人胡万军
优化与建议
隐私政策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35448号
( 京ICP备19053597号-1,电话18600416813,邮箱1479971814@qq.com ) 了解Tax100创始人胡万军
优化与建议
隐私政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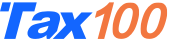
 【全网最全】31个省市!残保金政策汇编及申
【全网最全】31个省市!残保金政策汇编及申
 全网最全|2022年失业保险稳岗补贴政策汇总
全网最全|2022年失业保险稳岗补贴政策汇总
 2021年个税汇算容易出现哪些错误?税务总局
2021年个税汇算容易出现哪些错误?税务总局
 【全网最全】历史上最高规模退税减税!2022
【全网最全】历史上最高规模退税减税!20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