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小编荐语
本期栏目继续摘编评述近年来国外主要法学刊物刊载的财税法学术论文,选取美国杜克大学法学院主办的 Duke Law Journal 的共五篇文章,推出“税务规章的司法审查”专栏。
自1984年“谢弗林案”后,美国形成相对确定的司法尊重原则,即法院在行政诉讼案件中审查行政机关作出的对成文法的解释时,原则上应尊重行政机关的专业判断。但在税法领域,美国司法系统却坚持1979年“消声器案”确立的“税收例外论”标准,法院可依据税收法定原则对税收行政规章适用更严格的审查标准,而不同于一般行政法上的“谢弗林原则”。直至2011年“梅奥案”,联邦最高法院明确“对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保持统一方法的重要性”,表示不会“开创一种仅对税法有利的审查方法”,故法院对美国财政部或国税局制定的税务规章进行司法审查均应适用“谢弗林原则”。“梅奥案”并没有终结税务规章司法审查的理论争议,相反,司法标准的变动深化了学界对“税法与行政法之间的关系”“税收法定原则的价值内涵”“税务司法的功能定位”等问题的思考。 Duke Law Journal 曾于2014年举办了主题为“Taking Administrative Law to Tax”的学术研讨会,并于当年刊载了学者们提交的会议论文,其中支持或反对“税收例外论”的观点均有涉及,并包含针锋相对的论证理由。本期栏目提炼其中的精华内容,以飨读者。
德州理工大学法学院教授 Bryan T. Camp 回溯美国《行政程序法》颁布前的税收管理史,说明“税收例外论”的历史背景和合理性。明尼苏达大学法学院教授 Kristin E. Hickman 主张区分美国财政部和国税局基于筹集收入制定的规章和基于其他社会经济调控或监管目的制定的规章,后者应当适用与一般行政法相统一的司法审查标准。佛罗里达州立大学法学院教授 Steve R. Johnson 主张调和美国国税局裁决的司法审查标准与一般行政法上的“合理解释要求”。杜克大学法学院教授 Lawrence Zelenak 从不同角度为“税收例外论”辩护,认为税法有充足理由偏离于一般行政法。德州理工大学法学院教授 Richard Murphy 主张废除“税收例外论”具有节省司法成本的效果,法院还应进一步减轻行政部门就税务规章履行一般行政法的“通告评论程序”的负担。
目录
专栏 税务规章的司法审查
01 《行政程序法》之前的税收管理史
02 管理我们拥有的税收制度
03 合理解释与美国国税局裁决
04 终究,也许只是有点特别?
05 务实的行政法与税收例外论
专栏 税务规章的司法审查
1
《行政程序法》之前的税收管理史
A History of Tax Regulation Prior to the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 Act
来源 | Duke Law Journal,vol. 63, no. 8, 2014, pp. 1673-1715.
作者 | Bryan T. Camp(美国德州理工大学法学院教授)
行政程序法与税收管理的关系已经成为理论和实务界日益关注的主题。学界批评了美国财政部长期坚持的“根据美国《国内收入法典》(Internal Revenue Code)7805(a)条的一般授权发布的税务规章是《行政程序法》(the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 Act)意义上的解释性法规”的观点。文章通过回顾《行政程序法》颁布前的税收管理史,说明了这一长期坚持的观点的起源和基础。文章指出,《行政程序法》的一般条款适用于税收管理必须参考《行政程序法》之前的税收管理历史。
文章的目标是引导读者从立法规则和解释规则等抽象概念,转向对税收管理和行政法关系中术语来源的更具体的理解。首先,文章分析了目前税收征管过程中存在的授权制定规则现象。国会授予财政部长(Secretary)税务管理和执行税法的权力,财政部长又会将权力进一步下放给税收专员(Commissioner),专员也将这些职责中的一部分委托给其他下属。除此之外,国会还对财政部长实施了一般性授权(允许其制定“所有必要的规则和行政规章以执行税法”)和具体性授权(在《国内收入法典》的数百个具体章节中允许其制定解释性规则)。针对这一现状,目前的主流观点认为,税务规章在授权和发布上都不当规避了一般行政法原则的适用。文章则对这一主流观点进行了批判:该观点通过对《行政程序法》具体条款的遵守情况来衡量税收管理是否符合“行政法”,假定《行政程序法》是确定税收和行政法之间适当关系的起点,歪曲了《行政程序法》和《国内收入法典》之间的关系。文章认为,分析税务规则的正确出发点是在税收管理案件中建立的先例,而不应当是《行政程序法》。《行政程序法》是建立在已有的概念之上的,特别是“立法性规章”(legislative regulations)和“解释性规章”(interpretative regulations),而这些概念是在税收管理史的影响下纳入法律的。
随后,文章回顾了1789年至1862年的税收管理史。美国内战前行政法的一项重要发展是明确承认行政部门可以发布行政规章。早期的关税管理主要通过制定法律予以规范,财政部长则通过给征税员写信(circulars)来对征税行为进行指导。为了回应对部长权力的一些怀疑,1792年《关税法》规定“财政部长应根据他的判断,指导对关税和吨位税的征收”,这是1832年之前关于税收行政权力范围的唯一法定指示(statutory direction)。1832年《关税法》第一次明确授权财政部发布被称为“规章”的指导意见,但是附加了一系列限制性条件:不能与法律抵触;财政部长应在总统的指导下行使该项权力;制定者有向下一届国会报告依据授权制定的规章的义务。除了上述两种指导形式(通知和法规)之外,当《关税法》的实施出现问题时,为了在纳税人起诉时免除个人责任,征收员会写信给部长寻求指示,部长往往采取通知的形式答复决定(decisions)。由此产生的问题是,征收员只在有助于免除他们的个人责任时才会遵守财政部的决定。故而,国会在1842年《关税法》中增加的“we really mean it”的法规,明确地赋予财政部长解释法律的权力,并将执行并落实财政部长的指示明确为征税员的法定义务。1842年《关税法》加强了关于税收行政管理制度的两个重要概念:其一,财政部根据一般授权发布的决定是对法律进行解释的方式。其二,税务指导是针对财政部雇员的行为,而不是针对纳税人的行为。
最后,文章分析了1862年至《行政程序法》颁布前的税收管理史。美国税收制度发展的重要节点是1862年,国会为获得收入以资助内战通过了新的税收法案,创造了大量新的税种,并创建了国内税收局(BIR)作为财政部的一个下属办公室来监督征管人员。为满足管理征税行为的需要,国会对BIR专员进行一般性授权,允许他们制定实施税法所必需的指示、规章等。由此,形成了财政部长发布的税收指导意见和BIR专员发布的次财政部指导意见两种旨在为实施税法而制定的规则。之后,文章从权限和发布两个方面分析了上述规则。在权限问题上,文章从三个方面切入:在涉及酒厂的民事案件中,法院区分了财政部长发布的规则和对BIR专员发布的规则,认为后者没有法律效力;在涉及特定消费税的刑事案件中,法院则认为BIR专员发布的规则并不必然因其专员的行政级别而影响其效力,其同样是为了解释法律,没有不当地修改法律的内容,具有法律效力;法律变化时,涉及未更改部分法律内容的行政规则的效力存在疑问。发布问题则涉及如何及时透明地发布税务指导意见。进一步而言,这些问题促进了在《行政程序法》颁布之前税收管理的三项重要的理论发展:(1)重新颁布学说(the reenactment doctrine);(2)追溯性学说(the retroactivity doctrine);(3)立法性规章和解释性规章的界分。但在《行政程序法》之前,唯一合法的税务规则是解释性规则(不能超出解释范围进行立法)。到1924年,一些国会议员重新提出了国会在1832年《关税法》中使用的观点,即规章制定权原则上只得在不与法律抵触的情况下行使,但会议报告以没有必要为由删除了草案中的相关表述。
1928年,国会在对关联公司征税问题上明确授权财政部长对确定纳税主体作出实质性决定:1928年《收入法》第141条指示专员经过财政部长同意可以制定必要的规章,以确定关联公司集团的纳税义务。国会的这种做法在之后的立法中变得更加普遍。
通过上述讨论,文章指出,读者不应独立于历史和法律适用的行政背景来解释《行政程序法》中术语的意义。相反,读者可以从税收管理的历史出发,对税务规章作为解释性规则的渊源有进一步的认识和了解。

2
管理我们拥有的税收制度
Administering the Tax System We Have
来源 | Duke Law Journal, vvol. 63, no. 8, 2014, pp. 1717-1770.
作者 | Kristin E. Hickman(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法学院教授)
鉴于筹集税收收入的特殊性,美国财政部时常声称其颁布的规章不受《行政程序法》中对立法性规章的“通告评论程序”(notice-and-comment rulemaking procedures)的限制。美国国会也在行动中表露出类似的倾向,例如国会刻意限制对《反禁令法》与《国内税收法典》第7421条的司法审查,且明确赋予财政部颁布溯及适用规章的权力。法院也经常援引税收收入的重要性以论证“税收例外论”。在Bull v. United States案中,美国最高法院以“税收是政府的生命线,其征收效率与确定性是迫切需要”为理由,对纳税人挑战税款评估和征收的行为予以限制。鲍威尔大法官撰文指出《反禁令法》的主要目的是使得政府尽快评估与征收税款,尽可能地减少执法前的司法干预。简言之,税收例外主义的捍卫者强调税收收入的重要性以支持税法不同于一般行政法的结论。
但是,国税局不可能也永远不会完全保持价值中立,税法在筹集财政收入的过程中通常伴随着对社会福利或规制目标的追求,例如个人所得税的累进税率是对社会不平等问题的补救,企业所得税使得政府可以规范企业活动或限制企业政治权力。事实上,税收作为政府规制工具箱中的工具之一,税收制度设计并非完全基于理性税基的概念,而是出于鼓励或遏制某些行为的动机,如国税局允许慈善捐款在税前扣除,而拒绝将贿赂、政治游说、过度补偿等支出予以税前扣除。文章指出,筹集税收收入并非财政部与国税局的唯一关注内容,税式支出(tax expenditures)越来越成为实施政府政策的主要工具。更进一步,文章认为,近十年来基于其他目的制定的税务规章正在迅速增加,庞大而复杂的税式支出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国税局并不像是一个税款征收机构,而更近似于政府规制机构。
基于财政部颁布规章与国税局税收执法的共生关系,文章通过对2008年至2012年五年间财政部拟议和颁布的共449份规章进行实证分析,观察税收筹集职能与其他规制职能二者的比例关系。文章将收集到的税务规章按照其主要内容分为税式支出,平价医疗法案(Affordable Care Act),雇员退休收入保障法案(ERISA),免税组织,政治融资,公司税,遗产、信托、不动产税,消费税,合伙企业税,个人税,雇员税,就业税与税收征管等十二个大类,并将其归集为三个子集。其中,前五个类别属于代表完全政府规制目的的子集,第六至八个类别属于兼有税收筹集与政府规制目的的子集,第九至第十二个类别属于完全税收筹集目的的子集。以规章数量、项目数量或文件页数为统计口径进行分析,可以看出,无论以规章数量或项目数量为标准,有关税式支出的规章占到六分之一以上,不具有税收筹集目的、归属于第一子集的规章总计达到近三分之一。如果算上兼有税收筹集与政府规制目的的第二子集,那么具有其他政府规制目的的税收规章将超过一半。若以税收规章的文件页数作为标准,则上述两个占比均将进一步提升为40.8%与66.8%。换言之,财政部与国税局将大量资源投入其他规制目的的规章制定,而非单纯出于筹集税收收入的目的。
因此,文章认为上述实证研究有三方面潜在意义:第一,诚然筹集税收收入具有重要性,但法院可以对《反禁令法》的税款评估与征收作出狭义解释,对超出保护范围的、基于其他规制目的的税收规章依据《行政程序法》开展执行前司法审查(Pre-enforcement Judicial Review),国会也应当重新审视并适当缩小《反禁令法》与《国内税收法典》第7421条的保护范围,使得财政部颁布的税务规章与其他行政法规的审查标准趋向一致。第二,虽然本文实证研究并没有评估税收规章的生效日期,但本文结论也侧面表明应更审慎地考虑财政部与国税局颁布具有溯及效力税务规章的权力,例如仅保留防止滥用税收制度与纠正程序性缺陷的税务规章的溯及效力,而使得基于其他规制目的的税收规章与一般行政法规保持一致。第三,利用税收制度实施财政支出安排(即税式支出)根本上是一种制度设计的选择,但国税局一方面需要筹集充分的税收收入,另一方面又要承担减轻家庭贫困、增进社会公平、提供医疗保障、监督非营利组织、促进经济增长等国会赋予的目标,已经从一个简单任务导向的征税机关转变为具有综合规制职能的政府机构。考虑到财政收入与支出之间本就存在竞争性的张力,应用税收政策工具可能只能取得次优效果,国会应当考虑是否可以对国税局进行机构重组。

3
合理解释与美国国税局裁决
Reasoned Explanation and IRS Adjudication
来源 | Duke Law Journal, vol.63, no.8, 2014, pp.1771-1834.
作者 | Steve R. Johnson(美国佛罗里达州立大学法学院教授)
文章观察到,美国联邦法院的判例表明了司法机关认可“一般行政法可以适用于税收征管领域”的观点,由此引发“行政法领域的’合理解释要求’(Reasoned Explanation Requirement)是否可以适用于国税局裁决”这一问题的思考。
当前,美国的税务专业人士并不十分认可将国税局视作行政裁决机构的观点,国税局所作裁决也一般不被视作行政法意义上的裁决。但从理论层面来看,终局行政行为需要满足两个条件:终局性与权义确定性。文章认为,根据以上标准,国税局所作的诸多裁决都可以满足这一标准。而且,文章还观察到美国联邦法院的近期判例也在声明“一般行政法可以适用于税收征管领域”。因此,作为最终行政行为的国税局裁决可以适用行政法规范,且应当应当遵循《行政程序法》中所规定的司法复审中的“合理解释要求”。
为了强化这一观点的说服力,文章还讨论了国税局四种主要的裁决类型——补税裁定(Deficiency Determinations)、 预险征收裁决(Jeopardy and Termination Determination)、催收正当程序裁决(CDP Determination)和信托基金追偿罚款裁决(Trust Fund Recovery Penalty Determinations)。文章认为,这四种主要类型的国税局裁决和其他部分类型的国税局裁决,都属于行政法层面的终局行政行为。
文章又着重对“合理解释要求”进行论述,阐述了其法定依据、后果、理由、成本以及相关案例。文章认为,《美国法典》第5章第706条是“合理解释要求”的法定依据,且根据该条规定,若行政行为是“任意的,反复无常的,滥用自由裁量权的,或者不符合法律的”,法院可以据此判定行政行为无效。文章还分析了《行政程序法》颁布前、后两个时间段内的经典案例,并指出法院对行政裁决审查态度从温和转向严厉,法院认为行政机关应说明行政裁决的政策前提(policy premises)、理由和事实支持。这一“合理解释要求”适用于所有行政机关及其行政行为,但解释需要达到何种程度才算合理并没有公式可循,需要依据具体情况进行判定。在违反”合理解释要求”时,行政机关需要采取相应的措施进行补救,否则行政行为可能会被判定无效。文章还总结了设立“合理解释要求”的理由,主要分为三大类:宪法方面的考虑、政治过程方面的考虑和决策质量方面的考虑。但文章并没有给出一个“一刀切”的结论,其并不认为《行政程序法》的“合理解释要求”应当直接适用于全部的国税局裁决。
文章通过当前国税局裁决实践情况的分析,进一步指出国税局裁决已经存在其特定的实质解释要求。通过利益衡量的方式,文章认为在国税局裁决中引入“合理解释要求”并不一定是利大于弊。主要理由如下:一是国税局裁决现有的解释要求与司法复审所主张的”合理解释要求”,在细节层面的差异较大;二是进一步提高国税局裁决的解释说明标准,并不会带来预期的收益,相较之下,转移举证责任的规定可行性和效果更佳;三是此举可能会打破横向公平,因为国税局裁决现有的解释要求是普遍适用的,而司法复审中的”合理解释要求”是个案单独适用的。
文章最终给出了明确的结论:基于法律的审慎考量与利弊衡量,“合理解释要求”在当前实践中仅可适用于部分类型的国税局裁决,在后续的实践和研究中还需尝试调和“合理解释要求”与国税局裁决解释要求之间的矛盾。

4
终究,也许只是有点特别?
Maybe Just a Little Bit Special, After All?
来源 | Duke Law Journal, vol. 63, no. 8, 2014, pp. 1897-1920.
作者 | Lawrence Zelenak(美国杜克大学法学院教授)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梅奥案”中认为,税务规章的司法审查同样应适用“谢弗林原则”,这被一些学者认为是“税收例外论”的丧钟。文章在梳理了“税收例外论”发展的背景和反“税收例外论”的论点后,从三个方面为“税收例外论”进行了辩护:首先,并非仅税务专业人士认为税收领域是特殊的;其次,和其他领域的专业人士宣称其所在领域法律的特殊性一样,“税收例外论”并非“特例”;最后,文章从一般原则适用的层面给出了“税收例外论”的其他辩护。
文章开篇介绍了“税收例外论”的提出及其相关的法院判例发展和学术争论。自1984年“谢弗林原则”被确立为行政规章的司法审查标准以来,该标准是否可以同样被适用于税务规章的审查就一直存在争议。1994年,Paul Caron教授以“税收短视”(Tax Myopia)指称“税收特别”的观点造成了税收与其他部门法的区隔,并从全球视角全面驳斥了税收具有特殊性的观点;12年后,Kristin Hickman教授指出“税收例外论”聚焦司法审查中对税务规章给予特殊司法尊重的问题,同样认为其导致的封闭效应使得税务专业人士忽视了其他领域的发展成果。为此,文章希望为“税收例外论”提出与前述两点驳斥意见相对应的辩护。
文章第二部分梳理了“反税收例外论”的论点。第一,文章从税法专业角度解释了“税收例外论”,明确以下讨论非基于“税法中的税收优惠”视角或“国际税法语境下美国税法特殊性”视角,而是指税法的特殊性所导致的某些跨领域通用规则不适用于税法。第二,文章整理了Caron教授的观点逻辑:①“税收例外论”存在于认为税法特殊的立法历史会影响其法律解释的行政部门中,体现在未将“谢弗林原则”适用于司法审查的法院中,并表现于税法学界的讨论中。②暗示了“税法短视”的原因可能是税法本身的复杂性,特别是《国内收入法典》最为明显。第三,文章简列了Hickman教授反驳“消声器案”中“税法应适用弱司法尊重”这一观点的思路,包括反驳了“税法在惩戒严厉度方面具有类刑法性的特点”“税务部门需要保证财政收入目标实现”“税法起草具有极强的专业性”等规范论点。相应地,作者在第二部分结尾肯定了“谢弗林原则”对税法领域的适用,并回应了Hickman教授的反驳意见。
在梳理了“反税收例外论”论点后,文章第三部分从三个方面对“税收例外论”进行了辩护。首先,文章认为并非仅有税法专业人士持“税收例外论”立场。从整体来看,无论是大众流行文化(以Roseanne、Ozzie and Harriet的剧集为例),还是其他专业的高知(如爱因斯坦),亦或是法学院的教授与学生,都普遍持此观点。从“谢弗林原则”的适用来看,不仅是法官本身有意避免接触税法案件或在不同案件中采用不同的审查标准,“梅奥案”之前的相关方(税务律师或政府机构)或出于诉讼策略或考虑部门利益,均倾向于采用忽视“谢弗林原则”的策略。其次,作者从“主题例外论”(Subject-matter Exceptionalism)的角度论证了其他领域的专业人士亦宣称其所在领域法律的特殊性。部分学者的文章提出在一些专业化程度更高且存在大量判例法的领域(如劳动法、社会保障法、环境法)中,学者和法官会主张选择忽略“谢弗林原则”的适用,并且建构该领域特有的司法尊重标准。Richard Levy和Robert Glicksman的文章特别指出了这一现象的归因——“谷仓效应”(Silo Effect),即由于代理成本(Agency Costs)、交易成本(Transaction Costs)和信息成本(Information Costs)的存在,可能导致一些领域产生偏离一般行政法原则的先例。最后,文章从一般原则适用的层面试图证立“税收例外论”的实质。仍以Hickman教授对财政部和国税局反纳税人偏见的论点为例,其论证结构其实说明了“税收例外论”只是一种标签(Labels)而非实质(Substance)。在司法审查中,对所有具有机构利益、处于对抗地位且可能存在机构偏见的特殊情形都可以适用弱尊重的司法审查标准。从更广义而言,这恰是一种更普遍的司法审查标准架构——包含两种司法尊重标准的一般规则,其根据是否有特殊情形存在而分别适用。换言之,“所有法规都将适用相同的解释方法,但方法之间的取舍将取决于特定法规在连续统一体(Continuum)中的位置,税法不过更极端”。至此,传统“税收例外论”被去标签化,税法得以在更普遍的意义上获得特殊性。
文章第四部分呼吁从更广义视角来看待“税收例外论”背后的特殊规则适用于其他法律领域的普遍性问题,并强调了税法的特殊性并不仅在于其复杂性,借用美国前国税局局长谢尔登·科恩(Sheldon S. Cohen)的话作结:“实际上,税收就是生活,一旦你了解它,就将拥抱生活的所有精髓——贪婪、政治、权力、善良、慈悲”。

5
务实的行政法与税收例外论
Pragmatic Administrative Law and Tax Exceptionalism
来源 | Duke Law Journal Online, vol. 64, no. 21, 2014, pp. 21-35.
作者 | Richard Murphy(美国德州理工大学法学院教授)
对于支持或反对“税收例外论”的各种观点,文章认为,法院和学界应该考虑行政法规定在重要领域适用的混乱历史,重视“税收例外论”的实用主义和灵活性。由此出发,文章重点讨论了两个问题:“谢弗林原则”是否适用于财政部根据一般性授权颁布的行政规章,以及财政部发布上述条例时是否应该经过《行政程序法》规定的“通告评论程序”。
首先,文章指出,最高法院在“梅奥案”中对“谢弗林原则”适用漏洞的修复,即用形式主义的方法来简化司法尊重理论的适用,以低成本解决了一个不必要的理论复杂化问题。法院解释法律的权力与法院尊重行政机构作出的合理的法律解释(statutory interpretations)之间并不矛盾。通常,法院会考虑机构的专业性(Moore案),保护法律稳定和信赖利益,行政机构解释法律时考虑是否周全、推理是否有效、前后是否一致(Skidmore案)等来证明司法尊重是正当必要的。在“消声器案”中,法院指出,如果一项行政规章是由那些被认为了解国会意图的人对法律进行的实质性解释,那么它可能具有特别的效力。在“谢弗林案”中,法院确立了“谢弗林原则”,其两步测试法要求法院在审查一个机构对其管理领域的法律的行政解释时,应审查国会是否对有关问题直接发表过意见,如果国会没有,只要该机构的解释是“可允许的”(permissible)即为合理,应予以肯定。法院对这种司法尊重给出了两种不同类型的解释——一种是源于授权(authority),另一种是源于能力(competence)。一方面,法院宣称,一个授权法案中的模糊语言表明国会隐性授权(implicit delegation)相关行政机构解决该问题。另一方面,法院认为尊重行政机构合理的法律解释是有意义的,因为行政机构比法院拥有更多的专业知识,承担更多的政治责任。在“梅奥案”中,法院面临的问题是,财政部根据一般性授权,经过“通告评论程序”后发布的条例是应当适用“消声器案”中的司法尊重标准还是“谢弗林案”中的普适性审查标准。法院放弃了前者,指出其“并不倾向开辟一种只适用于税法的司法审查方法”,而应统一适用“谢弗林原则”。法院得出结论,国会对财政部的授权使其法律解释具有法律效力,而财政部通过“通告评论程序”来发布有关规章,援引了这一权力。因此,“谢弗林原则”适用于该规章的法律解释,该规章也因此具有法律效力。文章认为,最高法院在“梅奥案”中的做法是非常明智的,这一解决方法的成本很低,将“谢弗林原则”应用于财政部的一般授权规章,除了简化辩护状和意见书的撰写外,在最终判决结果上不会带来任何影响。
其后,文章将重点转向对“通告评论程序”适用漏洞修复的问题。文章指出,《行政程序法》中“通告评论程序”是因为法院的重塑而变得严格,积极地对财政部适用该程序要求会带来高昂的成本。“梅奥案”确定一般授权性行政规章可以具有法律效力,但前提是其发布需要遵守“通告评论程序”。对此,文章认为,在对财政部的一般授权性规章适用“通告评论程序”之前,法院应该认识到弥补“通告评论程序”适用的漏洞的成本可能相当昂贵,而造成这种代价的主要原因是法院通过对《行政程序法》进行极富创造性的解释,使得遵守“通告评论程序”事实上变得非常严格。1946年《行政程序法》仅仅设想了一个简单的﹑要求不高的体系,用于向公众收集有关立法规则的信息和意见。法院则对此要求进行了重塑,大幅扩充了相关部门就拟议规章对外公告通知的义务、对法院认为任何重要的评论作出回应的额外义务,构成法院对行政规章的入侵性、任意性的审查形式。此外,“立法性规章”与“解释性规章”的边界向来十分模糊,法院从来没有能够设计出一个明确的审查流程来确定哪些规章需要履行“通告评论程序”,而哪些规章不需要。因此,法院应当运用其在其他领域行政法上的创造性和灵活性,以避免将有争议的程序负担强加给财政部。一种可能的路径是,法院运用其司法创造力,重视税收的特殊历史和需求,对行政法上的“解释性规章”采取宽松、灵活的认定方法,将一般授权性规章归类为“解释性规章”,从而避免强加给财政部和国税局“通告评论程序”的过重负担。
通过上述讨论,文章最终得出结论:对财政部颁布的一般授权规章适用“通告评论程序”的后果可能是不幸的。法院不能无视明确的法律,即使适用该法律会带来不幸的政策后果。但是,相关的行政法没有明确到排除法院以关心后果的务实精神来塑造和实施这一法律的空间。法院应通过扩大对“解释性规章”范围的认定,避免将“通告评论程序”要求强加适用于税收领域一般授权性行政规章,以免造成行政部门过重的程序负担。

整理/杨佩龙、林溢呈、扶琬萍、罗仪涵
排版/张 旭
审核/张 旭

北京大学税法研究中心
Peking University
Center for Tax Law

长按二维码关注我们 |
-

|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35448号
( 京ICP备19053597号-1,电话18600416813,邮箱1479971814@qq.com ) 了解Tax100创始人胡万军
优化与建议
隐私政策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35448号
( 京ICP备19053597号-1,电话18600416813,邮箱1479971814@qq.com ) 了解Tax100创始人胡万军
优化与建议
隐私政策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35448号
( 京ICP备19053597号-1,电话18600416813,邮箱1479971814@qq.com ) 了解Tax100创始人胡万军
优化与建议
隐私政策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35448号
( 京ICP备19053597号-1,电话18600416813,邮箱1479971814@qq.com ) 了解Tax100创始人胡万军
优化与建议
隐私政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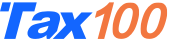
 【全网最全】31个省市!残保金政策汇编及申
【全网最全】31个省市!残保金政策汇编及申
 全网最全|2022年失业保险稳岗补贴政策汇总
全网最全|2022年失业保险稳岗补贴政策汇总
 2021年个税汇算容易出现哪些错误?税务总局
2021年个税汇算容易出现哪些错误?税务总局
 【全网最全】历史上最高规模退税减税!2022
【全网最全】历史上最高规模退税减税!20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