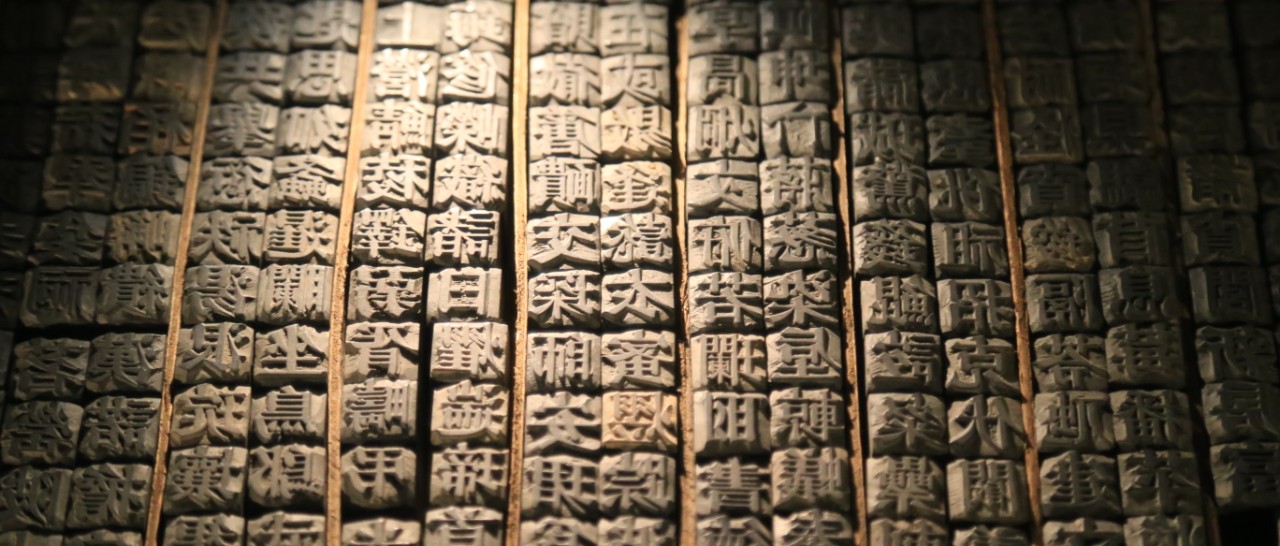|
|
史 卫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英国史学家汤因比认为文明的卓越出自艰辛,挑战才能真正激起具有创造性的应战。我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水旱震蝗螟霜雹疾疫各种自然灾害频繁,史不绝书。汤因比指出:“人类在这里所要应付的自然挑战要比两河流域和尼罗河的挑战严重得多。”中华文明就是在与各种自然灾害的斗争中发展壮大起来的,古代国家就是我国先民战胜自然灾疫的产物。先民们在抵御自然灾害的过程中,建立了集中财物、物资储备、协助生产的机制,逐步形成了我国古代独特的税收制度和思想。
一、抗灾防疫的需要对税收制度产生和发展的影响
(一)抗灾防疫的共同需要是促进税收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人类文明史上,防灾、赈灾、灾后恢复等公共需要往往是推动重大税制改革的契机。马克思曾提出东方国家的起源不同于西欧类型,是建立在履行社会公共工程基础上的,是“以贡赋的形式获取剩余产品并主管灌溉、交通等公共事务”。恩格斯亦指出:“政治统治到处都是以执行某种社会职能为基础,而且政治统治只有在它执行了这种职能时才能持续下去。”
我国古代税收制度的产生可以追溯到传说时代大禹治水成功后的恢复生产的制度安排。大约四千年前,地球出现了一个小冰期,气温变冷,洪水肆虐。地质考古表明,这一时期我国和世界其他很多地方都普遍出现了异常洪水地质记录。世界很多民族都留下了应对这场大洪水的传说,如希伯来人的诺亚方舟、印度人的摩奴之舟、迦勒底人的鸠什特拉舟,都是借助某种工具逃难,然后大难不死劫后余生的人们重建家园。只有我国是积极治水救灾,并在治水成功后积极进行灾后重建。大范围的治水需要专门的规划,需要用职能分工和集中管理的方式大规模组织人力,这就促使了氏族社会的质变和集中化权力的产生,推进了古代国家的形成,并建立了最初的财政和税收制度。《尚书·禹贡》开宗明义地说:“禹别九州,随山浚川,任土作贡。”禹在治水过程中,把天下划分为九州,根据各地不同土质和物产状况,建立了最初的税收制度。禹被认为是我国第一个朝代——夏的建立者。《史记·夏本纪》称:“自虞夏是,贡赋备矣。”即是说从夏朝开始,我国有了比较完备的税收制度。
近年来,随着地质考古工作的进展,新出土的文物、新发现的文献让我们能够对这段传说有更深刻的认识。2002年发现的《遂公盨》铭文中第一句就是“天命禹敷土,随山浚川,乃差地设征”,将大禹治水后建立赋税制度的记载提前到了西周中期。古人说:“大水之后必有大疫。”大禹治水的过程,也是一个抗疫防疫和环境整治的过程。上博简《容成氏》描述了这个过程,称经整治后,九州方可居处,“疠疫不至,妖祥不行,祸灾去亡”。我们从考古遗址也可以看到一些大洪水前后的变迁状况:有了完善的排水系统、公用仓廪的建设,有利于公共卫生的改善和物资的储备。
《尚书·皋陶谟》记载,大禹在治水成功后,向舜帝汇报并提出帮助民众恢复生产的建议“暨稷播,奏庶艰食,鲜食,懋迁有无,化居。烝民乃粒,万邦作乂”。小范围的疏堵不仅无法根治,而且会以邻为壑,而大范围的疏导和治理,就需要设置泄洪区疏导洪水,需要充分调剂和分配粮食,较好地保障分洪后的基本生活。抗灾防疫及灾后生产恢复等需要也催生了税收制度。《容成氏》记载,在这一政策执行五年后,经济得到了恢复,“民有余食,无求不得”。
在聚居农业特别是养殖业发展以后,传染性疾病更容易传播,疾疫成为人类生存的最大威胁。当时人们对传染病已经有一定认识,如象形字的“疫”写作“  ”,《说文解字》解读为“民皆疾也”,就是百姓都被传染了。《字林》解释为“疫,病流行也”。《释名》认为“疫,役也,言鬼神行役也”。由于缺乏科学的认识,早期人类往往寄希望超自然的力量,通过巫术的仪式,沟通天人,促使上天或者鬼神为人间抗疫、消灾、降雨、赐福。部落领袖往往兼着巫的身份,不仅是政治领袖,也是群巫之首,也即“巫君合一”,承担着抗疫、消灾、赈灾、降雨、祈福等公共职能。大禹治水的传说中,我们也可以看到禹的一些巫术活动。这种巫术的思想模式也深刻影响了早期人类社会组织的形式和机制的构造。巫履行这些公共职能主要通过一系列复杂的仪式,关键环节在于祭。祭祀仪式实际也包含了一些公共卫生的基本工作,如清洗打扫,烧火硝、熏香等,以去脏防邪。随着人们对疾疫季节性规律的认识,除了在发生疫情的时候举行祭祀仪式外,也在特定的日期举行祭祀,祷告上天以求能预防疾疫。《周礼·天官》称“四时皆有疠疾”,《礼记》《吕氏春秋》等书都记载了不同的季节要举行不同的祭礼来向上天祈福。 ”,《说文解字》解读为“民皆疾也”,就是百姓都被传染了。《字林》解释为“疫,病流行也”。《释名》认为“疫,役也,言鬼神行役也”。由于缺乏科学的认识,早期人类往往寄希望超自然的力量,通过巫术的仪式,沟通天人,促使上天或者鬼神为人间抗疫、消灾、降雨、赐福。部落领袖往往兼着巫的身份,不仅是政治领袖,也是群巫之首,也即“巫君合一”,承担着抗疫、消灾、赈灾、降雨、祈福等公共职能。大禹治水的传说中,我们也可以看到禹的一些巫术活动。这种巫术的思想模式也深刻影响了早期人类社会组织的形式和机制的构造。巫履行这些公共职能主要通过一系列复杂的仪式,关键环节在于祭。祭祀仪式实际也包含了一些公共卫生的基本工作,如清洗打扫,烧火硝、熏香等,以去脏防邪。随着人们对疾疫季节性规律的认识,除了在发生疫情的时候举行祭祀仪式外,也在特定的日期举行祭祀,祷告上天以求能预防疾疫。《周礼·天官》称“四时皆有疠疾”,《礼记》《吕氏春秋》等书都记载了不同的季节要举行不同的祭礼来向上天祈福。
祭祀所需要的财物一般通过氏族公共土地和摊派来筹集。这种因公共需要的摊派是税收的早期雏形,先民对防疫的公共需要的迫切性和巫术仪式的神圣性,也促使了摊派由自愿走向强制,由随意性走向固定性,为税收提供了最初的正当性与合法性。
(二)在应对灾疫中建立与自然和谐的税收制度
我国先民不断从抵御各种自然灾害的实践中总结规律,探索人与自然的关系,逐步建立起与自然和谐的税收制度。
一是税制安排要遵天时。古人在农业生产活动中发现了一些天象和气象规律,认识到有些规律不可改变,只有遵循和利用这些规律,才能减少灾疫,更好组织生产。《礼记·月令》系统记载了每个月份生产活动的规律,并就相应的政府征税活动进行了安排,要求符合自然规律。如孟夏之月,“蚕事毕……乃收茧税”。孟秋之月,“农乃登谷……命百官始收敛”。仲秋之月,“易关市,来商旅,纳货贿,以便民事”。如果不按自然规律办,则会带来“虫螟为害”“民殃于疫”“民多疟疾”“民必疾疫”。《周礼》规定地方进贡,“春入贡,秋献功”。春季入贡,就是指诸侯征税完成后,还要一定时间整理和采购贡品,只有到春季才能到王庭上贡。而一般作物秋天就能收成,诸侯就可以向天子献上报表了。秦国《仓律》规定每年税收的统计数据十月就要汇总造册,上报中央内史。但是因为水稻比粟成熟时间要晚,所以水稻的税收无法统计在当年税收账簿里,只能统计在第二年的账簿里。在农业社会,税收制度遵循农业生产规律对保障农业生产和农作物产量及品质至关重要。在征收力役时,也要求“不违农时”。
二是税制安排注重保护生态环境。古代先民把保护生态环境作为预防灾疫的重要内容,并贯彻到税制安排上。《周礼》中记载当时设置了专门官员来掌管山林川泽等资源的保护和赋税征收,这在金文材料里也有很多反映,强调要“以时入之”“以时取之”“以时征之”,而且要“取之有度”“取之有法”。就是进入山林川泽获取自然资源有时间规定,获取要符合自然生长规律,而且要有度有法,不能砍伐小树,不能用细密的渔网捕小鱼,不能用有毒的箭射取动物。征税也要以时征之,征之有度。就是要合理使用自然资源,保护生态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如“角人掌以时征齿角凡骨物于山泽之农,以当邦赋之政令。以度量受之,以共财用”。《礼记·月令》规定,孟冬之月,“乃命水虞渔师收水泉池泽之赋”。仲冬之月,“农有不收藏积聚者,马牛畜兽有放佚者,取之不诘。山林薮泽,有能取蔬食、田猎禽兽者,野虞教道之,其有相侵夺者,罪之不赦。”就是说十月可以征收水泉池泽之税,但十一月天气冷,民众容易感染疾疫,百姓有蓄积不足的,可以放开山林供他们采集,不加禁止。如有侵夺他们的,还要予以处罚。
(三)以减免税促进灾后生产的恢复
在遇到灾疫后,古代政府为救济受灾民众并帮助他们恢复生产,在采取救治、赈济等措施的时候,也会根据灾情进行税收减免。《周礼》就提出,“凶札则无力政,无财赋,不收地”,即发生饥馑疫病就免除力役、赋税。齐桓公时,提出“岁饥不税,岁饥弛而税”,荒年时不收税,等饥荒缓解后再收。一般出现较大的灾疫,国家因为救灾会扩大财政支出,而减税又会带来税收减少。为了寻求两者的平衡,从汉代起,开始探索更精准的减税。《汉书·宣帝纪》记载,汉宣帝时,还是对遇到灾疫的地方全免赋役。《汉书·成帝纪》记载,汉成帝建始元年(前32),则规定田亩收入损失40%以上的才能免税。到鸿嘉四年(前17),汉成帝又规定除了损失40%之外,还需家庭收入3万钱以下的才能免税。绥和二年(前7),汉成帝将免税的家产标准提高到10万钱。东汉时,可能考虑执行时核实不易,免税时不再要求家产标准。唐代对免税标准又进行了细分,《唐六典》规定,损失40%以上的,免半;损失70%以上的,全免。到明清时,规定得更加精准,将灾户应纳地丁正赋分作10分,受灾10分者免税7分,受灾9分免税6分,受灾8分免税4分,受灾7分免税2分,受灾6分和5分者免1分,并制定了报灾—勘灾—定级—蠲赋的严格程序。明太祖朱元璋要求:“但遇灾异,具实奏闻”“令灾异即奏,无论大小”,以便政府及时采取救灾措施。因为及时救灾的需要,我国也因此有了世界上最详细的灾疫记载。
(四)多渠道筹集救灾经费
救灾,特别是重大灾疫,往往就不是正常年份的税收收入能解决的了。《史记》里记载文景之治时国库充裕,但是一旦遇到灾疫,政府就会遇到财政困难,无力救灾。对政府而言就有了非正常状况的经费筹集,即存在应急财政问题。这个时候,政府往往为把“量入为出”的财税政策转化为“计委量入”“量出为入”,采取更多渠道筹集经费。如卖官鬻爵、入粟授爵、交钱赎罪等措施。西汉元狩三年(前120),崤山以东遭水灾,民多饥乏,汉武帝先是开仓放粮,但是国库不足以应付。于是向豪强募集钱粮,但还是不够。于是先后推出了白鹿皮币、白金、算缗钱,此后又推出盐铁专卖制度。这些非常时期的措施,或鼓励民间捐助,或有限度介入市场,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政府非常时期的财政困难,为防灾救灾提供了必要的财力支持。
二、抗灾防疫的实践对税收思想的影响
我国古代抗灾防疫的财税实践也促进了传统以民为本的税收思想的形成,这些思想对古代国家治理和抗灾防疫起到了积极作用。
(一)积蓄救灾思想
我国古代先民在抵御灾疫的实践中认识到积蓄救灾的重要,在原始部落时期就建构起积蓄体制。《礼记》写道:“国无九年之蓄,曰不足;无六年之蓄,曰急;无三年之蓄,曰国非其国也。”所以,“冢宰制国用,必于岁之杪,五谷皆入然后制国用。用地小大,视年之丰耗。以三十年之通制国用,量入以为出。”汉代贾谊的《论积贮疏》里说:“夫积贮者,天下之大命也。”古代政府除了通过税收加强国家粮食储备外,还通过授爵、除罪、减税等方式鼓励民众捐粮增加国家粮食蓄积。隋唐建立义仓,通过征收义仓税贮粮备荒,义仓税按照家庭资产等级征收,上户一石,中户七斗,下户四斗。除了直接调拨储备物资救灾济民外,也有用储备物资去补贴医疗救济机构的。如北宋崇宁元年(1102),宋徽宗就下诏各地设置居养院、安济院和漏泽园,“给常平米,厚至数倍”。宋政府以常平仓的储备为基础实行低息放贷性救助措施,以帮助灾民尽快恢复农业生产。古代政府还利用国家储备来调剂市场,如战国李悝发明的平籴法、西汉耿寿昌发明的常平仓法,就是在丰年大量收购粮食加大储备,灾年再以平价售出,保持价格稳定。这些思想的运用既减少了政府建立储备的成本,又对社会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二)敬天修德思想
古代对疾疫及自然灾害缺乏科学的认识,往往将成因归之为天或者鬼神。如《大戴礼记》里说,“凡人民疾、六畜疫、五谷灾者,生于天”,认为是“天道不顺”造成的。我国思想史传统中的天是一个具有道德属性的人格化的“天”,其所降下的灾疫是一种警示,是一种对德政的诉求。这个天命是与民欲联系在一起的。《尚书·泰誓》说“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上天关心的是人民的疾苦,天命是以人民愿望为依归。这也就使统治者在遇到灾疫时,必须救济灾民,减免税收。清代雍正三年(1725)《谕地方水旱督抚据实速奏诏》里就一再申明“天人感通之理”,要求地方官遇到灾害要“抚据实速奏”,及时救灾,“尽人事以仰邀天鉴”。要求地方官要“兢兢业业,时存戒惧”,不能隐瞒迟报,“致使旱涝成灾,闾阎受困”。这种敬天保民的思想,是希望借助灾疫论来制约君权,使君主能施行轻徭薄赋、及时预防救治灾害的德政。
(三)养民思想
《尚书》记载大禹在治水时就提出了“政在养民”“民为邦本”的思想。《周礼》提出了“慈幼、养老、赈穷、恤贫、宽疾、安富”的“养万民”思想。《管子》提出了“老老、慈幼、恤孤、养疾、合独、问病、通穷、振困、接绝”的“九惠之教”思想。孟子提出“明君治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蓄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无死亡”。晋文公认为政府的职责就是要“施舍分寡,救乏振滞,匡困资无”。明代方孝孺对古代养民思想进行了系统论述,提出“人君之职,为天养民者也”,“用天之所产以养天民”。因为天地的资源“不能自察而用之”,所以需要君主和政府“导之以取之”,“资之以用之”,“俾有余补不足”。这种养民思想,为政府救灾减税提供了思想基础。清康熙帝多次强调“民为邦本”,“治天下之道,以养民为本”,要求“必以蠲租减赋除其杂派为先”。正是这种养民思想的影响,康熙帝还经常打破灾免时按分数蠲免的规定,有时按照灾情状况增加分数,有时直接免除本年全部赋税。宋代在减免灾民赋税的同时,还给予无税可以蠲免的人家发放救济。至和元年(1054),黄河修堤时发生疫情,宋仁宗下诏“如闻疫死者众,其蠲田税一年;若雇佣并客户无税可蠲者,人给其家钱三千”。
(四)节用思想
防灾抗疫都需要耗费大量的人财物,在其他支出方面必然就需要节约。上博简《容成氏》就记载大禹俭朴节用:“禹然后始行俭:衣不叠文,食不重味,朝不车逆,舂不毇米,羹不折骨。”在先秦诸子中,孔子提出“政在节财”“节用而爱人”。《老子》提出“去甚,去泰,去奢”,墨子更是系统论述了节用思想。康熙阐述了节用思想,认为在“量入为出”的理财原则下,国家赋税收入的数额是固定的,必须节用才能有多余的赋税施于民,进行蠲免钱粮,也就是“损上益下”。康熙帝指出:“国家钱粮理当节省,否则一遇灾荒蠲免,其军饷河工等项经费必致不敷。”也就是说要在遇到灾疫时能保证及时蠲免,统治阶层平时就必须节用。
三、我国古代运用税收政策抗灾防疫的启示
(一)应充分发挥税收政策在救灾和灾后重建中的职能作用
税收具有集聚物资、调节余缺、经济杠杆多重职能,在应对灾疫产生的危机面前能发挥积极作用。一是筹集资金职能。古代政府除了以税收手段筹集财政收入外,也运用税收等手段建立救灾的专用储备。二是社会修复职能。在灾情发生后,及时赈济和减免税收是帮助人民维持基本生活和减轻经济负担的重要手段。为了更好发挥税收政策的作用,历代政府还要求及时上报灾疫情况,以便政府及时决策。朱元璋还要求一遇灾情“即时飞奏”。三是杠杆职能。如汉代采取入粟授爵的办法,只要买到五大夫以上的爵位就能免除一个人的赋役。也就是鼓励有钱人家购买农民的粮食捐献国家,既筹集了救灾资金,又在一定程度上调节了贫富差距。再如宋代有牛疫发生时,通过免除牛税,鼓励商人前往疫区贩卖耕牛。
(二)以抵御重大灾疫为契机推动税收制度改革
重大灾疫的发生,容易凝聚各方共识,往往是推动重大改革、促进负担公平的契机。大禹在治水后,根据肥瘠程度制定不同赋税标准。鲁国因自然灾害连年歉收导致凶饥,推动“初税亩”改革,不分公私一律按亩纳税。汉武帝在推动灾后救济时,推动大亩制,在税率不变的情况下将每亩面积由100步扩大到240步,事实上降低了田赋,鼓励农户生产。同时增加工商业税收,增加财政收入。东晋南渡之初就遇到大规模瘟疫,于是将农业税按户征收改为按实际亩数征收。负担公平,不仅能更好减轻人民负担,也有利于维持社会稳定。
(三)非常时期应急之法应该有退出机制
对于重大灾疫带来的财政危机,必须有与之程度相适应的大规模的财政政策来应对,这是保持国家稳定、维持人民生产生活所必需的,但是对于非常时期的非常之法应有相应的退出机制安排。汉武帝时面对自然灾害和战争带来的财政危机,推出了一系列增加收入的措施,一方面保持原有税收体系的稳定,提出“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的原则;另一方面也指出这是应急政策,“为此者不得不劳民”,提出在危机缓解后,政策回归休养生息的方向。这一政策回归常态的规划,也带来了后来昭宣中兴的局面。
(本文为节选,原文刊发于《税务研究》2020年第8期。)
(完)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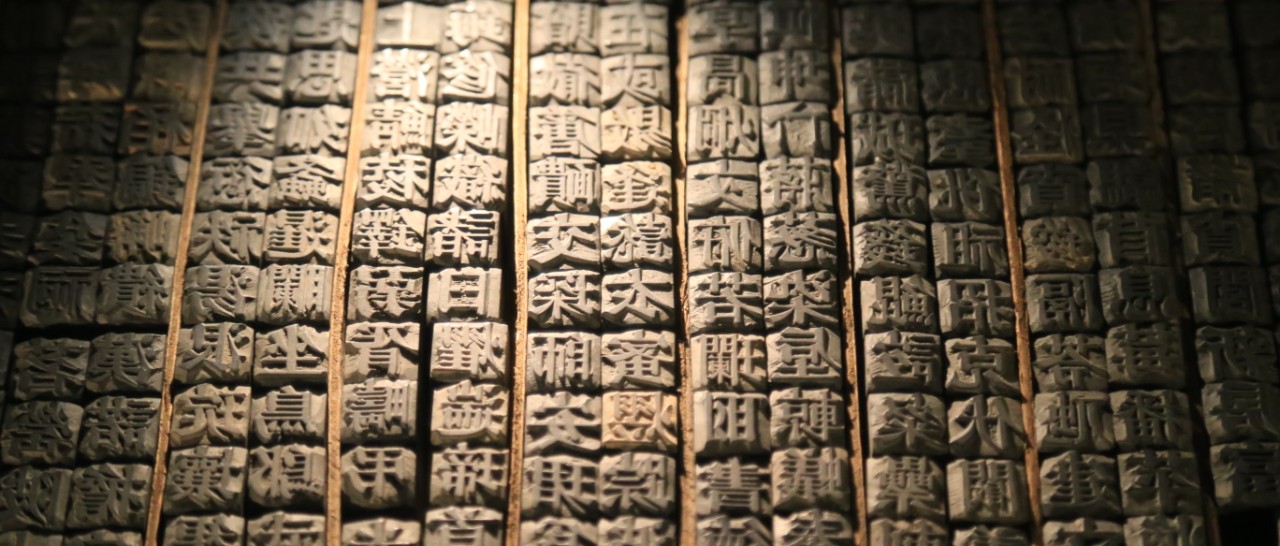
|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35448号
( 京ICP备19053597号-1,电话18600416813,邮箱1479971814@qq.com ) 了解Tax100创始人胡万军
优化与建议
隐私政策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35448号
( 京ICP备19053597号-1,电话18600416813,邮箱1479971814@qq.com ) 了解Tax100创始人胡万军
优化与建议
隐私政策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35448号
( 京ICP备19053597号-1,电话18600416813,邮箱1479971814@qq.com ) 了解Tax100创始人胡万军
优化与建议
隐私政策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35448号
( 京ICP备19053597号-1,电话18600416813,邮箱1479971814@qq.com ) 了解Tax100创始人胡万军
优化与建议
隐私政策

 【全网最全】31个省市!残保金政策汇编及申
【全网最全】31个省市!残保金政策汇编及申
 全网最全|2022年失业保险稳岗补贴政策汇总
全网最全|2022年失业保险稳岗补贴政策汇总
 2021年个税汇算容易出现哪些错误?税务总局
2021年个税汇算容易出现哪些错误?税务总局
 【全网最全】历史上最高规模退税减税!2022
【全网最全】历史上最高规模退税减税!2022